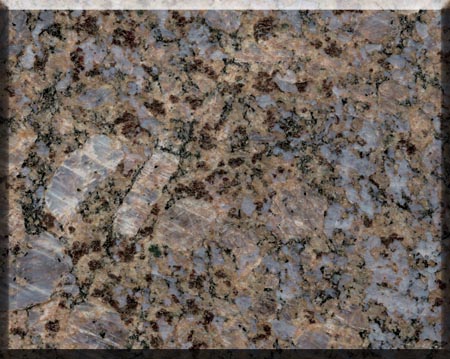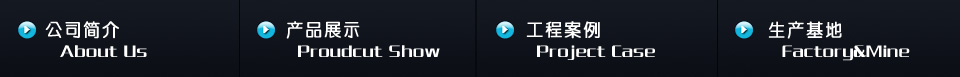
鲁迅说他是“石材”和“泥土”
犹记在故乡霍邱县老宅堂屋和西厢房的墙壁上,张挂着不少书画作品。中有先父韦佩弦(堂兄韦顺称他“四叔”)的一幅威猛的雄狮图,题为《怒吼吧,中国》,此画作于抗战时期。另有一幅是父亲在上海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攻读时和张大千合作的《松石图》,画面上有张大千的题词:“佩弦贤弟画十八公,我为其补石。张大千题。”字有美专校长刘海粟相赠的“佩弦先生学业精进”条幅和在渝时冯玉祥题赠的“爱人如己”墨宝。但他最为看重的是鲁迅为韦素园手书的碑文:
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,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。呜呼,宏才远志,厄于短年。文苑失英,明者永悼。
弟丛芜,友静农,霁野立表;鲁迅书。
父亲常说,鲁迅最喜爱的两个青年作家,一个是柔石,一个便是韦素园。父亲说这话时,甚为自豪,这是因为,韦素园是他的堂兄,长他一岁。韦素园原名“崇文”,父亲原名“崇仁”,后改名佩弦,韦丛芜原名“崇武”,素园和丛芜是亲兄弟。青年时期,父亲进了上海美专研朱墨作春山,而素园和丛芜二兄弟则在鲁迅的指导和支持下创办了“未名社”,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1920年,在“阿芙乐尔”起义炮声的鼓舞下,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下,上海建立了革命组织“社会主义青年团”,其宗旨是培养一批革命生力军,并从中遴选出类拔萃者去苏俄学习。为此,先办了一所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。此时,正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韦素园被送到上海进校学习。从各地选送来的还有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蒋光慈、曹靖华、彭湃等二十余人。1921年,组织上为他们办了为隐蔽身份的经商护照,安排他们自费赴苏学习。当时素园的大哥在安庆任职,他汇了一笔钱给素园作川资。夏天,他们乘坐由上海吴淞口开往日本长崎的客轮,再换船到海参崴。
其时,俄国内战在西部已经结束,但在东部海参崴一带,外国帝国主义的残存武装并未肃清,本土白匪猖獗,战事不断。据曹靖华在《往事漫忆》一文中所记,在韦素园一行由海参崴乘车去伯力时,带队的同志郑重叮嘱:“环境复杂,斗争严酷,红白难辨,凡事务需小心、沉着、机智而果决。每人所带机密证件,千万妥藏。路上不遇真正红军,既不能暴露,也不能丢失。暴露了丧命,丢失了不能入境。”素园他们刚登上开往伯力的火车,便遭遇了惊魂的一幕。这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引起了在车中巡逻的士兵的注意,他们荷枪实弹围了上来,搜查盘问,咄咄逼人,令素园一行个个悬心吊胆。就在这发悬千钧之际,一位同行者的秘密证件被搜了出来,大家都以为大难临头了。那群俄国兵仔细地审视证件,又用俄语相互交流。倏然间,他们面露喜色,张开双臂热情拥抱这群衣衫简朴的中国学生,并一迭声地呼叫:“达瓦雷西!达瓦雷西!”原来他们是苏俄红军!素园他们大喜过望。后来,曹靖华以这段艰辛而危险的旅程为素材,创作出话剧《恐怖之夜》。
克里姆林宫的那颗红星终于闪耀在眼前!素园他们个个欢呼雀跃,热泪盈眶。几天后,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,素园一行虽非“代表”,但被会议组织者安排与代表同食共宿,并可旁听会议。就在这次大会上,他们有幸聆听了列宁所作的关于俄共革命策略的报告。
大会结束后,韦素园他们被分到东方劳动大学学习,该校校长由斯大林兼任。学校生员多来自东亚,中国学生专设一班。这是一所政治大学,教材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》,还要学俄文,参加军训。学习很紧张,生活也十分艰苦。萧劲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:“那时真是饿得难受,我们的课堂设在四层楼上,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,可是上四层楼真是困难啊!冬天穿一件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衣服,晚上睡觉时,一个挨着一个,大家挤在一起取暖,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。”就是在这样的艰苦中,韦素园宁肯忍饥受冻,也要挤出点钱去旧书摊购买马列著作、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俄新文学书籍。这些书后来带回国,便是鲁迅见到的“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”。
由于语言上的障碍,共产国际指派以记者身份先期至苏的瞿秋白来校担任翻译和助教。瞿秋白到莫斯科后,根据所见所闻所感,写出了报告文学《赤都心史》和不少散文随笔。韦素园、曹靖华、蒋光慈也都热爱文学,于是他们在一起谈俄罗斯作家和文学,谈苏俄文学,甚是投缘,成了亲密的同志和挚友。受瞿秋白的影响和启示,韦素园选定了今后的人生之路:研究介绍苏俄文学。1922年,学业未竟,同学中吴宝鄂、廖化平生病难再坚持学习,韦素园和曹靖华毅然放弃宝贵的学习机会,护送两位同学回国。
韦素园回国后,到北京与在此读书的弟弟韦丛芜会合,又联络上了同乡台静农和李霁野。1924年,素园大哥在江苏常州病逝,他的经济来源断了,生活开始窘迫。他借了一间小屋栖身,靠煮字谋生。小屋位于沙滩新开路5号,在北京大学对面,这便是鲁迅所见到的“一间破小屋子”,后来成了“未名社”编辑部。有一学期,北京大学邀请鲁迅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,只要鲁迅开课,韦素园他们便慕名前来旁听。其时,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已经问世,他成了韦素园这样的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。
韦素园他们读鲁迅的作品,听鲁迅讲课,得机会便向鲁迅请教。师生们熟了之后,鲁迅下课后常到那间小屋里坐坐,和韦素园他们亲切交谈。当听了韦素园讲他的经历和理想后,鲁迅以为他有“宏才远志”,十分赞赏,并产生了信任感,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。当时鲁迅正在编两种丛书,即《乌合丛书》和《未名丛书》,前者收创作,后者收翻译。但当年的读者对译著不太热心,所以是否编下去,鲁迅颇踌躇。素园兄弟和台静农、李霁野知道后,毫不犹豫地向鲁迅表示,他们愿意翻译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。鲁迅当即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商量,决定将《未名丛刊》从北新书局划出,交给素园他们去办,并成立“未名社”——关于社名,鲁迅的解释是,不是“没有名目”,而是“还没有名目”,就像孩子“还未成丁”。1925年9月,在鲁迅的亲切关心和悉心指导下,“未名社”成立,成员便是霍邱县叶集镇的四个青年人。《未名》首期推出了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《出了象牙之塔》,次年又创办了《莽原》半月刊,创刊号上刊出了鲁迅的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。关于未名社,鲁迅曾作这样的说明:“未名社的同人,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,但是,愿意切切实实的,点点滴滴做下去的意志,却是大家一致的。而其中的骨干就是韦素园。”
素园因为健康状况不佳,不能去学校上课,也就顺理成章地为未名社“守寨”,从校对到改稿,从收发到财务,他一肩挑。除了为他人作嫁,他自己还要抽暇翻译、写作。无论你什么时候走进这间小屋,总能见到他伏案工作的身影,那仿佛是一座固定的雕像。在未名社创业的六七年里,素园和同仁编辑出版了二十四期《未名》半月刊,四十八期《莽原》半月刊;出版的创作丛书《未名新集》中,有鲁迅的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和杂文集《坟》,韦丛芜的诗集《君山》,台静农的小说集《地之子》和李霁野的小说集《影》。翻译方面,有鲁迅的《小约翰》和《出了象牙之塔》,韦素园的《黄花集》和《外套》,韦丛芜的《穷人》、《罪与罚》、《格里佛游记》、《拜伦时代》等,李霁野的《不幸的一群》和《黑假面人》,还有曹靖华的《第四十一个》、《白茶》和《烟袋》。鲁迅对这些出版物的评价是:“在那时候,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。”
由于长期清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,素园日见清瘦,全身乏力,并开始咯血。经医生诊断,肺部显现巴掌大的空洞,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,便是“绝症”。但他依然抱病坚守在编辑岗位上吐着余丝。延宕至1927年,这时鲁迅已离开北京去了厦门、广州,便由丛芜、静农、霁野将素园护送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养病。鲁迅得知素园患病,极为挂念,在信中叮嘱素园:“兄咯血,应速治,除服药打针外,最后是吃鱼肝油。”这样仍不放心,又在另函中提醒: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,倘若技痒,要写字了,至多也只好译译《黄花集》上所载的那样短文。他还不断给韦丛芜他们写信,打听“素园病已愈否?”愈则“甚喜”,否则,“素园兄又咯些血,实在令我忧念……”1929年5月,鲁迅北上省母,念念不忘的是看望素园。5月30日,鲁迅在韦丛芜他们陪同下,专程坐汽车去西山看望了素园。对于这次探病,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:“素园还不准起坐,因日光浴,晒得很黑,也很瘦,但精神却好。”但接着他笔锋一转:“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画像……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——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——便觉得心脏一缩……”
在远离市声的西山,韦素园缠绵病榻,日日咯血,人比黄花瘦。但是他以战士般的舍命精神倚枕笔耕,全力完成年轻生命的最后冲刺:翻译高尔基、契诃夫、安特列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和《托尔斯泰的死和少年欧罗巴》,写了十多篇散文随笔,辑成一册《西山朝影》,作诗二十余首编成诗集《山中之歌》。此外,还写下了不少杂文和几十封致友人的信。
素园的病是日益加重了,到了“咯血盈盆气若丝”的危境。他预感到大限将至,特选了一本自己翻译的布面装的《外套》托李霁野寄赠在上海的鲁迅。书上题字是“鲁迅先生惠存。素园敬赠。霁野代题字。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。”这本书成了永久的纪念。素园逝后两年,鲁迅又想起那本叫人感伤的《外套》:“素园逝去,实足哀伤,有志者入泉,无为者在世,岂佳事乎。忆前年曾有布面《外套》见赠,殆其时已有无常之感。今此书尚在行箧,览之黯然。”随后,鲁迅又写了《忆韦素园君》寄托哀思:
“是的,但素园绝非天才,也非豪杰,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,或名园的美花,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,园中的一撮泥土,在中国第一要他多。”